|
蘇州博物館新館奠基,緊鄰拙政園、忠王府 ,隆重熱烈的場面,讓人很難想象曾經有過的爭議。11月5日上午,頗受關注的蘇州博物館新館工程舉行奠基儀式。江蘇省委副書記、省長梁保華、世界著名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和夫人盧愛玲女士,以及眾多官員、著名專家,前來參加奠基儀式。 貝聿銘在奠基儀式上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蘇州是中國有名的水鄉,最重要的是治水,其次是綠化;蘇州已走過了能治水、能綠化這一步。接著就是建筑,路子很重要,規劃第一。”話鋒轉到了博物館新址上,他說:“這塊地很重要,特別有挑戰性。我們的文化保護區就在里面,拙政園在新館址的后面,忠王府在它的左面,在這里建筑不容易。”他介紹說,前天有4位院士從北京來跟他交談,有很多好的意見,大部分都是關于傳統的問題,怎么拿出這塊地,讓拙政園、忠王府與將來建成的新博物館打成一片。這是很不容易的。 貝老希望將來與蘇州能有很好的合作。“做成一個建筑不是容易的。我們要想辦法走這條路,希望有小小的成功。” 短暫的發言竟用了3個“不容易”,大師的嚴謹作風可見一斑。 奠基結束后,梁保華陪同貝聿銘和夫人,參觀了蘇州博物館新館設計展覽。參觀中大師興致勃勃。他還向梁省長提議,將拙政園前的平江路建成像上海南京路上的步行街,此地還可以建成上海的新天地。 世界頂級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在退休12年后重新出山,在被自己稱為“圣地”的地塊上———蘇州博物館新館,承受“人生最重要的挑戰”,他要把圓滿的“句號”畫在故鄉的土地上。經過一年多的緊張工作,貝聿銘順利完成了蘇州博物館新館的方案設計。今天,呈現在人們面前的這個設計方案,生動體現了蘇州傳統建筑風格與現代建筑手法的結合。 新博物館屋頂設計的靈感來源于蘇州傳統的坡頂景觀———飛檐翹角與細致入微的建筑細部。然而,新的屋頂已被科技重新詮釋,并演變成一種奇妙的幾何效果。玻璃屋頂將與石屋頂相互映襯,使自然光進入活動區域和博物館的展區,為參觀者提供導向。金屬遮陽片和懷舊的木作構架將在玻璃屋頂之下被廣泛使用,以便控制和過濾進入展區的太陽光線。光線的層次變化,讓人入詩入畫,妙不可言。新館與拙政園相互借景,相互輝映,它將成為一代名園拙政園現代化延續。看新館設計,越看越有味道,會有一種震撼心靈的效果。 新館地塊分為三部分。中心部分是入口處、大廳和博物館花園;西部為展區;東部為現代美術畫廊、教育設施、茶水服務以及行政管理功能等,該部分還將成為與忠王府連接的實際通道。 兩院院士吳良鏞和周干峙對設計方案表示贊賞。他們認為,新館設計方案與原有拙政園的建筑環境既渾然一體,又有其本身的獨立性,以中軸線及園林、庭園空間將兩者結合起來,無論空間布局和城市肌理都恰到好處。全國著名文博專家羅哲文老先生認為新館設計是謹慎的,建筑與周邊環境融為一體,符合歷史建筑環境要求。 貝聿銘在世界各地設計的大型建筑至今已有100項以上。其中不少建筑剛剛建成的時候,常常招來非議,但是不久又能夠成為當地人的驕傲,或者成為那個城市的一個標志。 貝聿銘最具爭議性的設計,是巴黎羅浮宮拿破侖廣場的透明金字塔。設計方案公布后,在法國引起軒然大波。用貝老的話說,事件簡直演變成一場“災難”,他在巴黎街頭遭到辱罵,被法國媒體譏諷為“貝法老”。他在公眾批評下幾乎失去所有顧客。但是密特朗總統力排眾議,還是采用了貝聿銘的設計方案。后來,金字塔和埃菲爾鐵塔一樣,成為巴黎的標志。 沒想到,貝大師在故鄉的“封筆”之作竟也出師不利,蘇州博物館新館選址引起極大的爭議。 今年8月,眾多媒體開始對此事進行跟蹤報道,有關人士紛紛發表批評觀點。中國園林界僅有的兩位院士陳俊愉和孟兆禎,曾分別向國家建設部園林處、國家文物局寫過信,表達了“希望重新選址”的看法。 令貝老深感欣慰的是,盡管這場爭論異常激烈,但處于言論“火山口”上的貝大師并沒有受到“蒸烤”。蘇州街頭沒有出現像當年巴黎街頭的一片責難聲。率先反對蘇州博物館新址的黃瑋說:“貝老的設計是不錯的,館址決策錯了。”言下之意,這場爭論與貝大師無關。故鄉人,故鄉情,還能說什么呢? 而蘇州市民對蘇州博物館新館設計也大多肯定。方案于今年8月6日至12日向市民公示并征求意見,投票結果顯示,93%的市民對新館設計方案表示滿意。 據了解,蘇州博物館新館占地總面積約10666平方米,包括拆遷在內總投資3.38億元,2005年底建成。 |
蘇州博物館新館奠基貝聿銘封刀作受爭議
2006-06-12 3989 0 39
39
評論區(0)
正在加載評論...
相關推薦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首爾新店設計:由多層停車場改造的現
2025-08-26 1992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coHouse 弗洛里亞諾波利斯島住宅設計
2025-08-28 1929 -
 行業資訊
行業資訊
Lamett樂邁石晶產品硬核測評:零醛、
2025-09-03 191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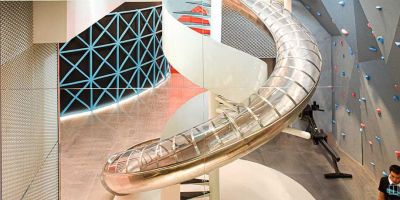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RAMOPRIMO MFIT SPACE 健身房設計:
2025-08-26 1848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以設計筑庇護:Casa Sadowski 住宅
2025-09-03 1778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Lilly Marques 設計助力:<哈克尼類
2025-09-05 1750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Hazard Studio 設計:舊車站里的 “
2025-09-05 1732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設計敘事:《兩院之家》的 “庭院導
2025-09-08 1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