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1926-) 哈爾濱人,文學翻譯家、作家、畫家。 曾任《世界文學》主編,致力于譯介和研究俄蘇文學藝術六十余年,在青年時代就曾經翻譯過俄羅斯著名文學大師屠格涅夫的散文詩,后來又翻譯過根據《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劇本《保爾·柯察金》、萊蒙托夫的《假面舞會》、瑪雅科夫斯基的《臭蟲》等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文人剪影》、《靈魂的歸宿——俄羅斯墓園文化》、《圣山行——尋找詩人普希金的足跡》,準備出版的有《俄羅斯大師故居》、《俄羅斯美術隨筆》等。 ■記者手記 “我這個人是隨著命運走,命運讓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先生用極濃的東北腔對我說。 不知道為什么,東北人說起話來仿佛格外誠懇和發自肺腑,透著一股豪爽勁兒。而那些他們所獨有的方言詞匯更具有普通話難以言表的趣味和魅力。 但是,東北方言卻一度成了先生做翻譯時的障礙。年輕時的他從未離開過日本殖民統治之下的偽滿洲國,以為全國人民都是這么說話,翻譯出來的作品也充滿了東北俚語,直到一位女作家提醒他語言不純。 有趣的是,談話期間,先生不斷地與我商量:“我做翻譯真的沒什么好談的。我想,要不我們談談我畫的畫吧,那更有意思一些。”說著,就起身拿出許多畫作出來給我看。 我說:“我發現您對繪畫的興趣要高于翻譯啊?”先生馬上點頭說:“是的,是的!是命運讓我做了翻譯家。” 我不喜歡做翻譯 高莽先生的筆名眾多,不過“烏蘭汗”這個名字卻稱得上大名鼎鼎。記得第一次讀到帕斯捷爾納克回憶錄《人與事》時,譯筆的美麗讓人驚訝,后來才知道譯者“烏蘭汗”就是高先生。 從我17歲公開發表第一首翻譯作品算起,譯齡已有60多年了。但最初,我并不愿意從事翻譯工作。我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占領的東北長大的。面對當時的現實,特別是看到奴相十足的“翻譯官”,十分厭惡。我覺得翻譯是給別人服務,替統治者做事。 我當時譯的是屠格涅夫晚年寫的《曾是多么鮮多么美的一些玫瑰》,這首詩的名字我到現在都忘不了,因為它給你帶來很多幻想。讀這首詩的時候好像有一點朦朧的希望在呼喚著自己,感覺挺神秘的。 那個時候,哈爾濱是偽滿洲國的一座城市,生活太黑暗了。要想去北京,還得辦出國護照。我活得很消沉,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也沒有革命意識。 1945年8月15日哈爾濱光復,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我在友協的報社工作,常常翻譯些俄蘇的詩歌散文,當時用過至少有七、八個筆名,其中一個名字是“何焉”,我是在反問自己:“我不喜歡做翻譯,為什么還在做?”1949年初有一天,路過哈爾濱的戈寶權同志想和當地的俄蘇文學譯者、研究者見見面。那時候,他很有名氣,是研究蘇聯文學的頭面人物。 我跟戈寶權說了我不想做翻譯的想法。他說那要看是給誰做翻譯,翻譯的是什么作品。我立刻領悟了,從此,我決心要為人民做翻譯,并起筆名“烏蘭汗”,即做“紅色的人”的意思。 全國都說東北話 高先生受的教育不多,才會有“全國都說東北話”的笑話。現在回想當年的軼事,除了感慨當時信息不暢,更需要注意的是那一代翻譯家的起點和生存環境。 我在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工作的時候,讀到俄文版《保爾·柯察金》。這是根據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改編的劇本,它對我的震撼太強烈了。你們沒法想象我當時的感動。而且,對比之下,更為自己感到慚愧,所以我把它翻譯了出來。 1947年,這部話劇被教師聯合會劇團選中公演,其中冬妮婭的扮演者就是我現在的妻子孫杰。那時大家都不了解蘇聯的情況,甚至人物的衣著打扮也都想象不出來。孫杰常常找我了解劇本里的一些問題…… 當時盡管演出條件差,但演出場場爆滿。解放初期,中國青年藝術劇院上演了這部戲,用的是我翻譯的那個劇本,導演是從蘇聯回國的孫維世,演員中有大名鼎鼎的金山、張瑞芳等人。劇本里有一些臺詞是東北話,青藝演出時作了改動,我是在哈爾濱土生土長的,沒去過其他地方,以為全國人民說的都是我們那種語言呢。 “母親中最可憐的母親” 阿赫瑪托娃是二十世紀俄羅斯最杰出的女詩人,也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現在回頭看看往事,除了荒謬,還需要一點警惕。 女詩人阿赫瑪托娃讓我重新認識了蘇聯詩歌。多少年后,我在一首詩中寫過阿赫瑪托娃是“母親中最可憐的母親,妻子中最不幸的妻子”,“背負著沉重的黑色十字,跋涉于凄風苦雨的人世,寒霜打僵了她的心,烈火燒盡了她的詩,她變成了影子,影子也得消逝……”1946年,蘇聯公布了《聯共(布)中央關于<星>和<列寧格勒>雜志的決議》,日丹諾夫為此作了專門的報告,大肆批判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那時,我們非常重視蘇共的文件。這樣一個有關文藝的決議和報告當然要翻譯出來,供我國文藝界學習。我譯了初稿。翻譯這個決議的時候,我并沒有讀過這兩位作家的作品。 這個決議和報告把阿赫瑪托娃罵得一塌糊涂,說她是“混合著淫聲和祈告的蕩婦和尼姑”,等等。我不但翻譯了而且還接受了決議的觀點。1954年,我隨著我國作家代表團去蘇聯參加他們的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和阿赫瑪托娃住在同一個旅館里,如果當時見到她,我一定會以決議和報告的精神來看待她……所幸,我們沒有見過面。現在我常常想,那個時候腦子怎么那么簡單? 文革后,我想了解阿赫瑪托娃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為什么要被罵作“蕩婦”。在北京圖書館借到西方出版的她的原著,書上還打著“內部參考”的圖章。一看才發現,她的詩歌毫無蕩婦的影子!特別是讀了她的長詩《安魂曲》之后,更感到她是一個非常富有正義感的詩人。我翻譯了一些她的作品,越來越喜歡。 我覺得我愧對阿赫瑪托娃。當年我畢竟翻譯過聯共(布)不切實際的決議和報告,而且還讓好多人都相信了那種極左的看法。后來我專程去過她和左琴科的墓,憑吊這兩位作家,也寫過文章悼念他們。 “怎么批怎么合適” 經常看到高先生為著名文學家作的畫像,這些肖像往往是形神兼似的。有時候不免會覺得高先生其實更應該是一位畫家。 解放初期,文藝界挨批的,我大概是第一人,只不過我是“小蘿卜頭”,不為大家所注意,而且在我之后文藝界又出現了幾個“反黨集團”大案。 1948年,哈爾濱響應中央的號召開展了反浪費運動。哈爾濱團市委《學習報》的一位編輯向我約稿。我畫了7幅反浪費的漫畫,刊出了4幅。后來,約我作畫的編輯傳達上級指示,要我檢討,說有人提出批評,指責我丑化勞動人民,是立場問題,對讀者有害等等。 新中國成立后,不知道是誰又把這4幅漫畫寄給了創刊不久的《文藝報》,說畫有問題。《文藝報》編輯部邀請了在京從事漫畫和文藝評論工作的部分同志,討論分析了我的漫畫,然后委托華君武和蔡若虹兩位美術界領導同志寫批判文章。 華君武在文章中對我充滿了關切,文章結尾提醒漫畫作者說,一方面要努力學習政治、堅持真理,一方面不要怕犯錯誤而擱筆。但我怕犯錯誤,擱了筆,決心再不用漫畫進行諷刺了,夾著尾巴做人吧。從此,我走上另一條路:只贊美,只歌頌。當時東北開展向蘇聯學習的運動,我畫了一本表現火車司機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連環畫,出版后我送給華君武同志,以為他會表揚我,沒想到他說:“你畫的不是連環畫,是給鑒定做的插圖。”“反浪費漫畫事件”之后,每次政治運動都要為此事進行檢討。因為我長在敵偽統治的環境里,在教會學校念書,家里又不是無產階級,屬于怎么批怎么合適的那種人。 華君武后來寫文章回憶那段歷史時說,批別人容易,批自己難。有一次我碰到他,他說:“當年我批你,可能扼殺了一個漫畫家。”我說:“多虧你批了我,也許挽救了一條命。”因為我了解自己的性格,說話沒遮攔,如果沒有那段經歷,以后的政治運動我不知道會犯什么錯誤。而且我意志薄弱,如果是突然遭遇到那些猛烈的政治運動,說不定就自絕于人民了。 不一樣的翻譯理念 高莽先生對翻譯的理解無疑是超前的,正是因為他的這種體認,《世界文學》為讀者帶來了更多、更新的外國優秀文學作品。 50年代茅盾先生主持《世界文學》雜志時,我作為翻譯陪他會見過蘇聯作協第一書記蘇爾科夫,那個人相當于我國的作協主席。茅盾告訴他說我們要發表美國作家海明威的《老人與海》。那個人說:“這部作品宣揚個人主義,對青年有毒害,還是不要發表為好。”茅盾表示和他的看法不同。 《世界文學》發表了《老人與海》,幾年之后,蘇聯思想界擺脫了禁錮,也發了這部作品。我當時就想,雖然我們好多東西都學習蘇聯,總說“蘇聯是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我們不一定全都不如人家,比如對《老人與海》的看法,茅盾就比他們看得遠看得深。 我在《世界文學》工作期間,也盡量介紹外國新的流派,有代表性的新作品。 我翻譯了一些作品。有的老翻譯家勸我翻譯經典的作品,但我不太愿意翻譯前人已經翻譯過的。第一位優秀譯者費的苦心是不容輕視的,而現在有股不正的風氣,有的人找出四五個前人的譯本,綜合一下,就成了自己的作品。 我也不愿意翻譯歷史已經定位成大作家的作品。我老想跟著時代走,在那些作家沒有得到定論的時候,測驗我自己的欣賞水平和觀察能力,判斷這個人有無前途,能否成為大作家,然后把他的作品介紹給我國讀者。 我沒能從翻譯實踐中總結出什么經驗,雖然字數在那擺著,年齡在那擺著,但有什么用吶?不過,像我這樣既做翻譯又畫畫,自己還進行創作,并且能得到讀者和觀眾認可,也算是幸運了。 (CSC編輯) |
高莽:游吟于翻譯與漫畫之間
2006-06-12 7223 0 76
76
評論區(0)
正在加載評論...
相關推薦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首爾新店設計:由多層停車場改造的現
2025-08-26 2059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coHouse 弗洛里亞諾波利斯島住宅設計
2025-08-28 2001 -
 行業資訊
行業資訊
Lamett樂邁石晶產品硬核測評:零醛、
2025-09-03 199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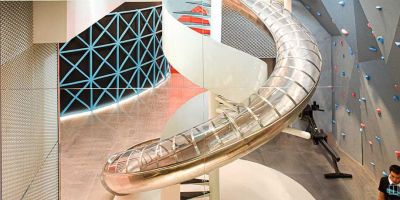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RAMOPRIMO MFIT SPACE 健身房設計:
2025-08-26 1923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以設計筑庇護:Casa Sadowski 住宅
2025-09-03 1846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Lilly Marques 設計助力:<哈克尼類
2025-09-05 1826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Hazard Studio 設計:舊車站里的 “
2025-09-05 1809 -
 設計欣賞
設計欣賞
設計敘事:《兩院之家》的 “庭院導
2025-09-08 1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