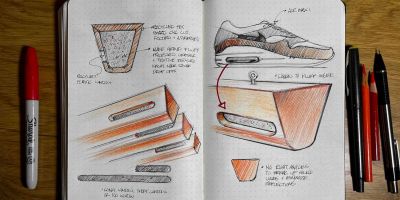“燒包”這個原來流行北方的俗語,如今在全球華人語匯中也流行無礙,有人認為現在是中華民族全體“燒包”。電影《手機》中嚴守一看到他的河南兄弟也掏出手機,就批評他們說:“倆燒包。放個屁都能聞到地方,還用得著打電話。”由此可見一斑。
在衣食住行用中,可稱為“燒包”的不勝枚舉。比如汽車,有車一族對好車的追求和評價標準永遠不會以環保為目標,而車展上商家吸引人眼球的也永遠不會是樸素耐用的車型,大眾高爾夫的兩廂車盡管在歐洲很流行,在中國卻是知音寥寥;豪華飯店那些用很復雜的程序泡發的魚翅燕窩的營養人人皆知十分可疑,那點鮮味也是許多其他東西勾兌而成,但是請客吃飯,大多數人還是不能免俗要點它;剛過完的中秋的月餅包裝,媒體這幾年也呼吁了很多次,要提倡節約不要奢華浪費,但是,月餅鋪張的包裝還是一年勝似一年;就說手中小小的手機,在中國的城鄉,其更新換代之快,時尚新款普及之廣,讓人瞠目結舌。我沒有去看過垃圾處理場,如果沒有回收,十年間那各種型號的廢手機堆積如山,一定十分壯觀;說到我自己,我已經很久未用鋼筆,墨水瓶早已干涸,我的女兒已經基本用一次性水筆寫作業;我們的居所周圍真的是日新月異,城市街道永遠陌生,建筑永遠是新的好,舊的必須推倒重來。最典型的例子,我的朋友20平米的客廳卻買了一個超大的等離子電視,因為距離太近只能將畫面縮小為4:3觀看。今天,電腦、音響、MP3等等,一切與時尚有關的消費,都無一例外被打上“燒包”的烙印。
“燒包”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美學特征之一。
民間說周圍人有兩個錢就不知如何是好,就“燒包”,就炫耀,就過度消費,就奢侈浪費,這僅僅是“燒包”的表象。看看網絡上對燒包的各自表述,就可知“燒包”與“裝飾”一樣,也有著相當的復雜性。就說前幾年曾經在網絡上廣泛關注的某高校的三層食堂裝觀光電梯之事,贊同者的意見就說如今中國教育投入充足了,超前點設計也沒什么了不起,我們總不能老是沉浸在八國聯軍蹂躪之痛的需要臥薪嘗膽的時代。還有相當多的“新”經濟學家,伙同房地產商一起,鼓吹“拉動內需”的消費,為了將老百姓的錢從銀行中轉出來,高房價、高消費的聲音,連同GDP的數據,一起甚囂塵上。這些經濟學家的理論是,“后現代”已經到來,中國要迎頭趕上,因為在全球化經濟時代,中國與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了。《聯合時報》署名常舟人的文章說:“‘燒包’是對個性消費、超前消費的一種肯定。燒包族以年輕人為主,他們已從有錢、花錢的層級上升到個性、時尚的層級,成為一支生機勃勃的消費大軍,這些人惟恐別人說自己沒有個性,巴不得別人把自己稱為‘燒包’。‘燒包’的詞義已經由貶轉褒”。
“燒包”由貶轉褒,在中國當代美學思想的發展上是一次令人沉思的轉變。歷史地看,“燒包”的美學觀從來未在各個時期成為主流,墨家的節用,儒家的文質彬彬,道家的自然脫俗,從來沒有使周圍人墜入“虛榮的”、“浪費的”、“表面的”燒包趣味中,即使在歷代奢靡君主當國時期,如李后主、宋徽宗等,也還稱得上是一種品位不俗的奢侈。“燒包”這種中國當代消費時尚,與西方富裕時期的所作所為不同,它不是致力于生活品質的改善,而是通過財富的揮霍和浪費,表現為麻木的、非理性的、生理復仇式的“阿Q”精神的延展,它其實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失落的背景下,商業經濟表面繁榮后犬儒主義思想抬頭的結果。
從民俗學的角度看,“燒包”的含義還可追溯到更深層的本意,北方民俗舊時祭鬼神,焚燒封成包的紙錢,也稱“燒包”。這種民俗其實南北方都有,今日看來,實在有“糊弄”神靈的意思,也是自欺欺人,今日鄉村舊民俗的恢復運動中的冥鈔、紙札的亭臺樓閣,究竟是慰藉故人還是安撫自己?仔細想想,確是一種民俗文化中心照不宣的庸俗表面的“人神溝通”現象,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問題是,這種“自欺欺人”的文化如果擴展到當代生活領域,更擴展到城市公共建設領域,這“燒包”可就真的燒大了。
在“燒包”文化的各種鏈條中,設計師只是中間的一端,他們常處在兩難之中,但對于商家的極端追求剩余價值的“原罪”和普通消費者作為盲目的被人逐鹿中原的“鹿”,設計師的良知,理性的專業素養和操守,又是極其重要的一環。但可嘆的是,有多少設計師忘了自己的尊嚴和使命,他們或者屈服于商家的“消費至死”的陰謀,或者干脆自己本人就是一個“燒包族”或者是“燒包”美學的追求者,正在充當著“同謀”的角色。可以預想,“燒包”隨著“文革”前后出生的一代人逐漸退出歷史主舞臺,而有可能更為大行其道,“燒包”美學或者干脆就是21世紀中國由獨生子女主導的主流美學也未可知。
可以確定的是,中國設計史“燒包”而會有一段奮不顧身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