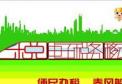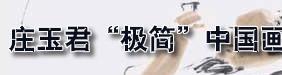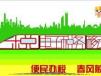“中國就應該是個實驗場”
從2008年起,MAD建筑事務所便策劃并組織了十一位國際青年建筑師,在花溪CBD城市中心設計中,展開了一次號稱“高密度城市自然”的“造城實驗”。于是在2009年伊始,我們便看到了一系列奇幻的效果圖:奇山異水的梯田之上,呈現出光怪陸離的建筑景觀。
先大規模地集中中外知名設計師,然后再因地制宜地“命題作文”。最近幾年這種“扎堆設計”的方式似乎成為一種潮流,也暗示著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始終沒有找到文化上達成共識的表達方式,因此,才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實驗。
曾有人有過這樣評價:“中國是這個星球上最激進的實驗場,就算是全世界最弱的建筑師,只要是他們來自國外就可以為所欲為。”作為新一代的中國建筑師,馬巖松顯然已經意圖擊敗這種偏見并開始在中國培育自己的實驗作品。
B:看到你在花溪的造城實驗,很多人都吃了一驚。
M:不知道你有沒有去過花溪,那是一個很美的地方,非常自然,多民族聚居。當地政府想把那里做成未來貴陽的CBD,一個集金融、文化、旅游觀光為一體的新的城市中心。所以我把它當作一次高密度城市自然的探索,一次集中了世界青年建筑師集體探索。每一位建筑師都基于他們對當地的自然環境與文化元素的理解,提出獨特的設計方案。目的是要達到它們如同自然生態環境有機和諧,并且形成復合多元的城市生活系統。
B:這是僅僅是一次概念設計,還是未來會在這邊土地上實現?
M:到目前為止,我只能說這是一次不怎么成功的概念設計,所以我們還要做第二輪、第三輪,甚至更多地設計嘗試。一旦成熟,它就會被實現。
B:你似乎并不排斥中國成為世界的實驗場這個論斷。
M:當然,我一直認為中國就應該是個實驗場。但是我強調的是實驗,而不是直接犯錯誤,更不是隨便來一個國外建筑師,做一個很不靠譜的設計,然后就開始蓋——都已經蓋成了,還算什么實驗呢?那就叫直接犯錯誤,不是實驗。
在英國的時候,我曾經參與過一個廣場的設計。很小的一個廣場,要是在中國,可能找個人畫一畫,就開始建了。但國外的建筑設計不是這樣,他們在開始設計之前要經歷很長一段時間的調查:不光是廣場做什么用,采光如何,甚至連每天有多少人從哪個口進,多少人從哪個口出,都有非常具體和嚴密的調查數據。然后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設計、推翻、再設計,才能從實驗進入到實踐階段。
在我看來,事實上在中國有些建筑師一輩子都沒有資格蓋樓,而是永遠畫圖,做設計,一遍又一遍地設計,做研究。就說花溪的造成實驗,你看我蓋了么?沒有,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我寧可只做設計。
去年汶川地震的時候,好多人說地震毀了許多城市,許多建筑,很可惜。在我看來,一次汶川地震算什么,你抬眼看看,全國都在蓋垃圾。
B:如果按照這種方式,這個設計的過程可能會很長,貴陽市政府會有耐心等嗎?
M:我相信他們會等的,因為這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嘗試。當然,如果他們失去耐心,不肯等,我想我們的這個概念設計還是會繼續。快速的經濟發展和日益膨脹的城市需求,導致我們在高速的低級復制之中生產出大量高密度城市,空洞、擁擠、缺乏靈魂。高密度城市自然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如果能夠實現,它會讓城市與周邊化境達成很理想的和諧狀態,它對中國城市的構架能提供很好的參考價值。
B:很高興看到最近幾年里,你的很多設計都陸續建成或者是開始建設了,不像MAD在中國最初的兩年,似乎反復都是在參與各種競賽和做一些概念設計。
M:對我來說其實那些所謂“不蓋”的設計也很重要,雖然我們現在的工作已經非常飽和,但我仍然堅持每年要做大量的“不蓋”的設計。梁思成的特殊性不在于他蓋了些什么,而是他對城市有著更高層次的規劃和理想。對我來說,那些“不蓋”的設計就是對更高層次城市理想的一種探索。有時候,一件完美的建筑產品反而不及一個幼稚而具探索性和建設性的概念更有價值。
平面設計
工業設計
CG插畫
UI交互
室內設計
建筑環境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33196557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