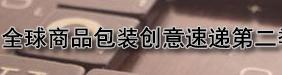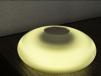21世紀經濟報道訪王澍
作者:21世紀經濟報道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
20年前,新疆人王澍逐漸習慣了西湖邊的生活,他還是一個美術學院校產公司的職員,后來他設計了這所學校新的校區。2年前,他公開展示了改變未來城鎮化人居的野心。在上海世博園內,王澍設計的城市實踐區項目為他贏得國際性的贊譽。今年他成為第一位獲得普利茲克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中國公民,該獎被譽為建筑界的“諾貝爾獎”。此前在西方受教的華裔設計師貝聿銘獲獎后,加速成為了全世界文化類建筑藍圖的執筆者。
世博園中王澍從寧波滕頭村移植的建筑形態,被評委會認為是“討論了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系”,而這與正在蔓延的中國城市化爭論有關。王在1980年代就在思考這類關系。他還在東南大學讀本科時,一年暑假,花了21天讀康德的《形而上學導論》,身處在火爐南京,他經常坐在寢室床上一動不動。王澍曾經更多自視為一個思辨者的角色。在他的課堂里,學生要寫毛筆字,讀《莊子》《老子》,下農村考察。他的思辨帶有批判性,很多時候外界看來也意味著邊緣化。
王本人并不同意自己被貼上完全學院派的標簽。在一次座談會上,他說,“我們在座的這些人,多多少少都是屬于在企業里面鬧革命的那種,而不只是簡單的學院派……我越到后來越有很大的疑問,我不僅是反學院,我甚至是反所謂的建筑學的建筑師,否則的話我也不會把我的工作室的名字叫做業余建筑工作室。這里面有一個基本的態度,就是我對整個學科的質疑。”
當時,滕頭村對未來的勾勒已經不缺少呼應。在世博園隔江的一角,湖南企業家張躍工程師36小時內建造起企業場館。他運用了公司自行設計的結構和材料。張過去的獨特形象在于不通過貸款迅速擴張他的中央空調制造線,但政府仍然決定支持或投資他的事業。當時張躍清晰地表明,遠大集團的業務將從室內空間擴展到這種空間的構建。張稱之為“可持續性建筑”。今年他希望在國內至少簽訂五個大區銷售商,年內建成1000萬平方米。在這之前,關于他要用這種技術建造亞洲第一高樓的項目信息已經廣為傳播。這是否會在政策和市場間達成平衡,目前還是未知數。
至少從學術文獻上看,中國建筑業還沒有系統性的討論過下一個20年。在歐洲和北美,建筑業應對2030年挑戰的提法已經屢見不鮮。歐洲建筑界技術平臺(ECTP)2005年就發布了遠景,他們認為未來的當地建筑業將由需求和知識推動。而幾年前加拿大進行的“挑戰2030”建筑設計比賽,則鮮明地將能耗危機擺上臺面。
在中國,很多人認為政府仍然是建筑人居領域最大的“甲方”。城鎮化還有多大空間,城市和鄉村的格局將如何演變,現在還沒有剛性的政策。在今年國慶以前,國務院副總理又向省部級官員專門講授了一堂城鎮化課程,他認為中國將從現有約50%的城鎮化率,進一步提升到發達國家普遍的70%左右。在下一段浪潮中,王澍的個人參與也許僅停留在畫面中的幾幀里,但他的想法代表了領域內一定范圍內的共識。
“人造歸屬感”都是失敗的
《21世紀》:您是如何看待今后20年中國城市建筑,尤其是居住類建筑的發展的?以及建筑師生存方式,空間利用,材料使用和城市化后果?
王澍:前些年,社會上流行大房子,現在這樣的房子少了,政府也意識到了問題,小房子、廉租房等等都更加多地出現。這是中國城市化的必然結果。我們國家的城市化,現在主要面臨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現有城市規模的控制。城市化在我國已經飽和了,我們擁有數量非常多的大城市,這些城市的規模都是世界級的。規模不可能無限制擴張,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城市有個運行費用的問題,到了一定規模,它再也無法維持自身的費用。我們現在的城市運行費用,如果沒有來自房地產業的收益,很難維持。這樣的狀態其實類似在吸毒,它是不可能持續的。現在我國的農業用地已經達到下限了,房地產業的圈地方式必須要停止。在這樣的前提下該做什么?我們可以對比日本。日本當年也是一樣,大家都想住在城市里,買大房子。現在,在東京能買個幾十平方的房子,就很開心了。
第二個,是鄉村再建設。在我看來,鄉村生活是更可持續、更生態也更有價值的生活方式。它是自給自足的,消耗很少。但現在的農民,基本上都是向往城市的。一個村里好不容易出一個大學生,就馬上移居到城市了。所以鄉村再建設需要我們整個社會的觀念大轉化。我們要建立一種鄉村和城市同等價值的觀念。德國就是這樣,它有許多的人是住在鄉下的,鄉村建設得很好,大家不會覺得低人一等。
觀念的轉化,涉及到中國當前的城鄉二元化。一直以來是農村支援城市,城市的發展是建立在農村的失血上的。要怎樣破除二元化,它也必然需要政策性的調整,比如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但是政策調整這個事情會有很多種方面的影響,沒那么簡單,我也沒有最終的答案。但是我認為,提出這個問題是重要的。
另外,鄉村再建設也是一個文化歸屬感重建的過程。整個西方現代城市規劃史在“人造歸屬感”上的努力,都是失敗了的。那些新建的城區,都是“睡城”,居民只是晚上回來睡個覺的,平時仍然都去老城活動,造成老城的擁堵。這也就是我說的城市郊區化的意思。
《21世紀》:很多人認為在中國地方政府是建筑規劃業最大的甲方,但理論上也可以說政府是公共意志的執行者,你現在依然在中國美術學院任二級學院負責人,還有很多建筑師在國企或事業單位體制下工作,你怎么看待未來中國建筑師的生存問題?
王澍:建筑師把自己定位成專業人士、服務業人員,是遠遠不夠的。現在中國的發展對傳統建筑文化的破壞那么大,為什么沒有人憤怒?這是因為建筑師普遍不思考。他們是這個社會潮流的同謀。
將來的變化發展,需要的是從下到上的覺醒,很多問題是體制解決不了的,要求的是思想上的變革。未來建筑師的生存方式會不會更好,我不敢說,但是會更多元。當年我開始做我的業余建筑工作室時,幾乎沒有同類,但現在漸漸就多起來了,將來會有更多的獨立工作室,有更多的獨立性、“業余性”。
中國美術學院建筑藝術學院院長。第一位擔任哈佛大學研究生院“丹下健三客座教授”的中國本土建筑師。2012年成為中國首位普利茲克建筑獎得主。
王澍:可持續的、更生態及有價值的生活方式
“用新方法繼承傳統”
《21世紀》:比起設計主體,很多人更期待今后建筑業在空間、材料使用上的發展。也已經有企業愿意為之下注投資,他們在推動政策和補貼方面是下了功夫的。但也有人說這種政策推動很難持續。
王澍:(城市建筑的)基本原則是節約。這也是由資源缺乏而被迫采取的。現在許多的高科技材料都是高能耗的。其實在歐洲這種高能耗建筑是很多的,這是中國不能模仿的。然后是要能反映當地的文化和氣候特征。 至于材料科技上的更新,其實對建筑不會有太大影響。因為建筑是一門相對比較成熟的技術,絕大多數建筑是給人住的,所以一定會比較謹慎,不會輕易采用新材料。把對未來的期待完全寄托在材料科技發展上是有問題的,不能指望技術一更新,困難就可以得到解決。
《21世紀》:我們假設近20年中國的城鎮化有一個既定模式,比如說它存在一個政府不得不尋覓級差地租的問題,還有戶籍和社保等相對滯后的制度,如果按照現有這種強大額模式發展,未來會變成什么樣?
王澍:后果很難預料。中國經濟長期處于大幅增長階段,但這樣的繁榮是很難持續的,增長的停滯必然會到來。所以我們的注意力必須要轉移。在前面階段的城市發展中,該有的硬件我們已經都有了,但是我們的軟件很差。城市都是車行的城市,不是步行的,人找不到可以好好走的路,都是給車走。其實參考全世界,這樣的失敗先例很多,西方一些大城市早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實行改善,我們還在重蹈覆轍。所以不出10年,城市發展模式一定會變。
在中國城市化后果的種種可能性中,最差的是拉美化,也就是貧富分裂。鄉村的人持續涌進城市,但是城市無法妥善容納他們,于是出現大量的貧民窟。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我說,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是簡單的事情,它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
《21世紀》:具體地分析呢?中國每天都在改變的政治經濟社會因素,有哪些會在今后一段時間影響和限制未來建筑人居發展?
王澍:在中國這樣的權力集中的地方,國家級的戰略決策非常重要。現在國家經常提發展文化,但這種發展以大量拆除為前提,這種狀況讓我毛骨悚然。比如新農村建設,它是鼓勵拆除的,它會補貼那種拆除行為。我認為我們現在必須無條件地停止拆除,不帶任何附加規則,必須馬上停止。這種情況下精英階層的作為非常重要。我做這一行,也會接觸很多弱勢群體,他們普遍沒這方面的意識。也有的人在農村苦苦守護,但是他們很無力,需要外界支援。這兩年討論國學的人多了起來,但這是虛的,無法在現實層面影響傳統生活方式。媒體應該在這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去呼吁對傳統文化的保護,為中國獲得尊嚴。
《21世紀》:你是否有一些我們可以體驗的作品,已經在試圖表達20年后中國建筑人居的應有范式?
王澍:我設計的中國美院象山校區其實就是一次對未來中國城市建筑生態的嘗試。有很多人問我,為什么要把象山校區的建筑群排得那么緊湊,中國其它高校通常都是零散的建筑,中間大片的草地,為什么我不那么做呢?因為我考慮到了中國的高密度人口。我考慮的不僅是學校里的這些人,這個校園的設計是具有通用性的。另外象山校區在材料的使用上堅持低能耗的原則,它是用新方法去繼承傳統。我們是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家,在這前提下,如何保持好的環境呢?大草地這種做法就不合適了。之前我做過一個商品房項目“垂直院宅”(錢江時代),設計時就給每戶都留了一個幾平方的陽臺用來做一些綠化。在資源限制下,用私人小花園代替大花園,這樣就挺好。我帶學生做過一個調研,結果發現整個杭州城,不需要有超過8層的建筑,前提就是建筑要密。
繼續閱讀:
編輯:shx
推薦
花邊
排行
專題
平面設計
工業設計
CG插畫
UI交互
室內設計
建筑環境
中國設計之窗 © 版權所有 粵ICP備09030610號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news@333cn.com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news@333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