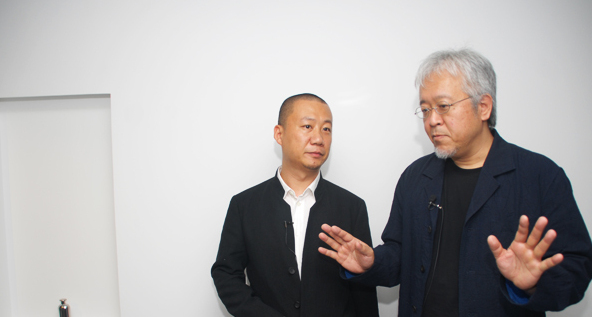空無一物的豐富性
和長次郎的“樂茶碗”的相遇,是在京都樂美術館。那種沖擊至今還鮮明地銘刻在我腦海之中。我完全被黑色渾圓的茶碗所吸引,癡迷地望著它,展示臺的玻璃罩都因鼻息起了霧。這個無光澤的濃縮體寂靜無聲,宛如吞噬了一切意義和能量。如果膨脹、擴張就是宇宙,那讓同一宇宙凝縮起來也許就是這般模樣。雖然它的造型簡潔,但是并不能稱之為“簡單”。因為這并不是通過科學性就能達到的美,棲息于此的是另一種審美意識。
在前一節中我講述了簡單這一概念的產生過程,它誕生于近代理性戰勝與權力密不可分的繁復圖案期間。然而,日本文化的核心審美意識“簡素”,并不是經過了與“簡單”同樣的歷程而產生的。我說過,簡單誕生于一百五十年前,如果回顧日本的歷史你會發現,其實早在這數百年前,與“簡單”非常類似的、極致簡潔的造型就已經隨處可見了。其中的典型就是長次郎的樂茶碗,以及保留在京都慈照寺的足利義政的書齋“同仁齋”——它被稱為現代和室的起源。這些與復雜性相對立的簡潔性中滿載了權力,與簡單有本質的區別。勉強來說,“空”即是虛空。那種簡潔性既不是探索造型科學性的成果,也不是偶然的產物。在這里,“空無一物”被有意識地設定為目標。人們掌握了“空”這一概念并加以運用,用空的容器來引人注意,并以此作為凝聚力。
如果日本的審美意識是資源,那么就應該積極地加以利用,但是與此同時,更重要的是了解它產生的原委。在這里,我繼續根據自己的經驗,來談談“空”誕生的背景。
我在京都茶室拍廣告的時候,遇到了樂茶碗。當時我在慈照寺東求堂“同仁齋”、大德寺玉林院“蓑庵”、武者小路千家“官休庵”等國寶級重點文物的茶室進行實地拍攝。置身于這些空間,我發現,被運用于這些茶室中的審美意識,與現在身為設計師的自己的感覺是相通的。特別是在足利義政度過晚年的京都東山慈照寺——通稱為銀閣寺——東求堂的書齋“同仁齋”,我忽覺茅塞頓開。
足利義政開始在東山隱居時正是十五世紀末的室町末期,算來已距今五百多年。通過茶道提煉出東山文化的千利休活躍的桃山時代,也就是十六世紀后半葉,這比包豪斯誕生還早了三百多年。
以簡樸為宗旨的審美意識的譜系在全世界來說都很罕見。因為復雜在權力的表象斗爭中稱霸了全球。在去繁就簡的意識變革中,應該有相應的原因。我認為它的起因或許就是應仁之亂這一文化遺產的燃燒殆盡波及了京都。
足利義政是室町幕府的第八代將軍。正如各種文獻中所記述的那樣,他缺乏政治能力,治國熱情低下。據說他熱衷修建宅邸、鐘情美術,愛藝術甚于江山。如果他能勵精圖治,妥善處理繼位問題,團結家庭,也許就不會天下大亂,也不會發生應仁之亂了。然而不可思議的是,義政將軍不爭氣的政治能力使得國家動蕩不堪,引發了大規模的戰亂,而日本文化也因此涅槃重生,走向了創新的道路。
簡單來說,應仁之亂就是演繹室町幕府權勢變弱全過程的超乎想象的大規模戰爭。戰爭歷時十年左右,戰火侵襲了歷史悠久的京都,這使當時的日本文化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
因為京都逃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所以年長的京都人所說的“之前的戰爭”指的是應仁之亂。這樣的說法讓戰爭聽起來很優雅,實在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是戰爭就是戰爭,其破壞本質沒有變。與被B29燃燒彈化為灰燼的東京一樣,室町幕府末期的京都,也因為飽受十余年的戰亂,大部分都被付之一炬。但和燃燒彈不同的是,破壞、掠奪這些人禍使得風雨飄零的京都雪上加霜。皇宮、將軍、貴族的宅邸也慘遭破壞、掠奪。期間,大到寺廟、佛像、建筑、庭院,小至畫卷、書籍,甚至衣物、綢緞,一切可以被破壞的不計其數的文化遺產都消失了。京都一度遭受了這樣的破壞,使得積淀深厚的日本文化幾乎被洗劫一空。
民間傳說,即使戰亂迫在眉睫,義政仍舊會沉迷于書畫之中,他就是這樣走火入魔般地沉迷于美的人。相反也正因此,他才應該更加清楚,被戰亂破壞的文化財富是多么巨大。經歷了特大損失之后,戰爭才宣告結束,如果古董書畫商看到了,想必會痛心地癱倒在地吧。結果義政把將軍的位子讓給兒子,自己隱居東山。可是到了這步田地,他依然沉湎于大興土木與藝術,現在慈照寺的一角,就建著他精心設計的東山御殿。然而諷刺的是,也是在這里,開創出了日本文化全新的敏感性。
足利義政在東山修建的東山御殿,可謂是集義政審美意識精華的大成之作。由于應仁之亂剛剛結束,可想而知當時的財政預算一定捉襟見肘,但是義政可不是會因為這種原因節約任何東西的人。他對國計民生置若罔聞,將僅有的一切投入到預算中,修建了自己晚年的居所。
然而它所表現的決不是奢華,而洋溢著簡潔、質樸的美。榻榻米滿滿地鋪了四張半。拉門將戶外的陽光過濾成斜射的間接光。隔扇上貼滿了典雅的壁紙。寫字的書桌和裝飾架都收拾得井然有序。打開書桌正面的拉門,庭院中的景致好像卷軸般,按比例截取后映入眼簾,完美得如同數學定理。義政并不是小心謹慎才選擇了這樣的表現。也許是因為站在權力巔峰探索美,加上應仁之亂的慘烈損失,他才抓住了某種全新的感知力的根據吧。
在此之前,日本的美術和家具絕不是簡樸的。地處歐亞大陸東方的日本,受到了世界各國文化的熏陶。日本身處世界的盡頭,任由各地強權制造的絢麗象征物傳入國內,對被稱為“唐物”的舶來品追捧不已,當時的日本應該呈現出了絢麗豪華的文化形式。最好的例子就是佛教傳入日本后,佛教文化也隨之興盛起來,于是就有了大佛開光法會等壯麗華美的文化活動。
曾經的日本文化應該對舶來品的精巧、別致倍加推崇,并且從中汲取了很多營養,日本文化曾經是這樣編織而成的。
而如今,我們已經無從知曉,那些親眼目睹了集中保存這些文物的首都京都被燒毀的人們,他們的心中流轉過怎樣的景象,產生了怎樣的領悟。但是,與其將華美的裝飾細節修飾一新,何不孕育一種全新的、能與絢麗相抗衡的極致素雅、洗盡鉛華的審美意識呢?我們可以想象到,正是以完全相反的、岑寂的極致樸素對抗舶來的豪華,日本才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感覺的升華。
空無一物,也就是“空白狀態”的運用就這樣開始了。在經歷了應仁之亂之后日本的感覺世界中,這美學上的揚棄,或者說革命此起彼伏。
世界各國都有喝茶的習慣。有時間喝一杯清香四溢的熱茶的人,一定懂得蕓蕓眾生的生命喜悅。在室町幕府后期,人們開始通過“喝茶”這種普遍行為,來開啟千姿百態的想象力的共鳴。而這一切的源頭就是“茶道”。勉強要說的話,其實喝茶不過是一個借口或者說是一個契機。人們將可以盛裝人的情感與想象的空蕩蕩的茶室設定為“空白狀態”,并加以運用。茶室只作最低限度的修飾,來幫助人們享受茶的樂趣,并以此喚起豐富的想象力。比方說在水盆中裝滿水,水面上零零落落地漂著幾片櫻花的花瓣。這樣的裝置會引發主人與客人的共同遐想,讓他們感到仿佛自己正置身于怒放的櫻花樹下。又或者端上一盆水果,賓主就能將夏日之感寄情于水果之中,聯想到一起在炎炎夏日享受清涼的情景。茶道的無窮妙趣就蘊含在這些裝飾之中。但是發揮作用的不是情景再現,而是一種“素簡”的創造力,它刻意控制整體裝飾,消除存在感的干擾,促使觀者主動地去修飾補充整個情景。
如果站在空白狀態的角度來看,我們也可以從“皇帝的新衣”這個寓言故事讀出完全相反的寓意。因為能夠將孩子眼中赤身裸體的國王看成穿著衣服的這種想象力,正是茶道之中的創造。赤裸裸的國王自信滿滿地披著“空”。因為空無一物,才能承受一切評價。
與之相同的還有使空間產生空寂的留白和張力的“插花”,以及融匯了人的情感,自然與人工結合的“庭院”。這種相同的張力來自“空”的美學,“空”引發人的聯想,并將人的意識投射其中。通過這次在茶室的實地拍攝經驗,我親身尋訪、體驗了這股力量運轉的場所。也因此,追根溯源般探尋到了與我們現代感覺源頭相通的美的脈絡與感性的源泉。長久以來一直有一個疑問困擾著我,雖然我了解西方的現代主義與簡單,但是總感覺和自己的文化有一種微妙的區別。而此刻,這個謎底也終于解開了。
與長次郎的樂茶碗在樂美術館的邂逅是一個句點。在結束一連串的攝影之后,我順路去了美術館。濃縮了一切的它就陳列在那里。
- 瑞典全新電視頻道TV12形象設計
- 趣味編程網站Codecademy新LOGO
- 法國著名水上運動品牌Tribord新LOGO
- 拉丁美洲最大的租車公司Localiza啟用...
- 溫良敦厚 Brassneck自釀啤酒品牌形象...
- 哈利法克斯(Halifax)全新的城市形...
-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塞米諾爾人隊新形象
- shiqi原創作品:貓咪形象的喜帖設計
- Dan Hoopert現代簡約花紋圖案花式字...
- MCBC妙集品牌原創作品:小古林海鮮特...
- 楊浦原創設計作品:EA品牌形象設計方...
- 蘇富比(Sohteby’s)拍賣行新LOGO
- 香港Astrobrights系列包裝設計(二)
- 北京李風體品牌策劃有限公司LOGO設計...
- 香港Astrobrights系列包裝設計(一)
- Ottawa Health Group品牌形象設計
- 德國Der ZIRKEL,der macht雜志編排設...
- New York Times Book 封面編排設計
- 以色列推出全新的國家形象標志
- 美國Kigo Kitchen快餐品牌形象設計
- 西班牙FELIX品牌包裝視覺設計
- 香港Flowergala餐廳視覺設計
- 西班牙小吃食品平面設計展視覺設計
- 香港K11設計商店2013圣誕促銷視覺設...
- 舊金山The Battery私人俱樂部形象設...
- 如果科技公司是球隊,他們的Logo是這...
- Houston Trueblood創意包裝設計
- 意大利Piadina Romagnola快餐店形象...
- 北京李風體品牌策劃有限公司LOGO設計...
- Processed Identity 創意品牌設計
平面設計
工業設計
CG插畫
UI交互
室內設計
建筑環境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news@333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