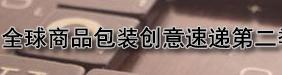雙訪張永和:警惕與診斷
作者:333cn.com 來源:333cn.com :
其二:建筑師該把城市的病癥說出來、說清楚
南方都市報
進入建筑領域三十多年,張永和舉辦首個個人回顧展。三十年前,別人提起張永和會說,這是張開濟的兒子。張開濟,新中國第二代設計師,作品有天安門觀禮臺、武漢長江大橋等。現在,張永和被稱為“中國現代主義建筑之父”。
9月29日,張永和回顧展“唯物主義”在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開幕,六個庭院般的模塊組成的胡同命名為“單車公寓”、“不理想城”、“無間造”、“無盡院”、“后窗”和“圣人書房”。代表張永和六個關注及實踐方向:居住方式、建筑秩序、城市化、傳統、感知和文化。
但展出中最吸引人的,是他在80年代至90年代所畫的建筑草圖、繪畫。黑白兩色的線條工整勻稱,既畫出了建筑美感,又把陰影涂抹得像表現主義電影。整個80年代并沒有人找他設計房子。他也是靠想象與圖紙贏得了一系列日本、美國的設計競賽的一等獎。
以前人們只知道長城腳下的公社、世博會的“魔方”,這次回顧展展出了張永和來時的路。
張永和說,建筑師是一種知識分子,得懂得生活是怎么回事,以及它應該是個什么樣。他說,在混亂的時代里如何蓋好一個房子、布好一個城市,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也是個社會問題。而建筑師,就該站出來發言和行動,因為“這是建筑師參與社會的方式”。
學建筑、留學都是父親的主意
“今天的學生看到的作為他們榜樣的建筑師都是在蓋房子,而我們那一代人看到的榜樣都在畫畫、寫書。像雷姆·庫哈斯當時是一個作家、思想家,所以我們也沒有必須要蓋房子的壓力。”
南都:你是1978年考上大學的,當時為什么選擇了建筑系?
張永和:其實我開始想學美術,可是我畫得太差了。1977年是“文革”最后一年,所有的美術學科和音樂學科是當時最難進的。很多人在自家學美術或者音樂。所以我就想,讀工業設計行不行?但是因為考生的整體水平太高,我還是進不去。親戚朋友一看,就說我畫畫沒戲。數理化我也不行。后來,父親比較嚴肅地跟我說:“學建筑也不用畫太好,數理化也不需要太好,你就學建筑吧。”那時候,最重要的是好歹也得上大學,對吧。
南都:這個理由挺好玩的,想不到張開濟是這樣對自己的兒子說的。
張永和:實際上就是這么回事,而且他說的一點不錯。這么多年后我認為就是這么回事(笑)。
因為在國內大家有一個錯覺,哪個科熱門了,就被誤解成哪個科需要高智商。但建筑不需要畫畫或者數理化特別好,也不需要高智商。這并不是說建筑容易,建筑并不容易,而是它需要綜合不同的知識的能力,這種能力孩子們常常沒有。所以實際上,建筑是沒有天才的,也是這道理。
南都:今年年初普利茲克得主王澍召開記者招待會,他形容自己就是沒有高智商,但有智慧感的一個人。
張永和:說起“智慧”,現在中國人基本不知道還有“智”和“慧”的區別。“智”就是機智,“慧”實際上是領悟的能力。其實學建筑的人需要對生活有更多的理解,他才能夠利用不同的知識,盡管每門都不深,但能夠融合利用。
南都:當你在大學里讀書的時候,國內建筑理論界的狀況是怎樣的?
張永和:在我們“文革”后第一批的學生里,“建筑學”這個詞是盡量不提的,因為談起“建筑學”就要談審美,而這就容易與意識形態掛鉤。老師只教我們做房屋的設計,而并沒有系統的理論。中國之前一些很有名的建筑家,比如梁思成、林徽因,他們把精力放在中國的古建筑的現場調研上,這是非常偉大的貢獻,可這并不是說他們有自己的理論體系。當然他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但是這些看法、對建筑的認識,在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后,就不斷地被政治運動打亂。他(梁思成)太想跟上主流意識形態了,不斷地調整自己,結果仍然左右都挨批,這是個悲劇。
南都:你是在1981年自費去了美國,這在當時是非常少見的。
張永和:這也是我父親的主意。我職業上關鍵的一些決定都是他建議的。從學建筑到留學都是父親的主意。另外他有個遺憾,就是他自己沒留學。當年他手續都辦好了,可是1949年他決定留下來,覺得以后也有機會去留學,后來挺后悔的。所以他就特別希望我和我哥都出去留學。
南都:但你家境很優越嗎?在80年代自費留學,簡直不可想象。當時中國人月收入才合幾美元。
張永和:當時自費留學不是現在這個概念,當時的中國社會情況,恐怕沒有一個人能自費。為什么呢?因為當時一個中國人能帶出國的是40塊美金。但當時是一個在美國的親戚做經濟擔保人就辦成了。靠獎學金和打工養活自己,在餐館做工,在建筑師事務所畫圖,等等。
南都:你這次個展中有不少80年代時期的草圖,有很重的現代主義痕跡。是初到美國受到的那種沖擊嗎?
張永和:實際上我在中國時沒有接觸過現代主義建筑和現代美術。剛才也說了,在中國當時理論界避談建筑學,可它的教學中帶有明顯的古典主義審美觀念。而且它不講理論,直截了當地講建筑,反而也是現代主義的觀念。到美國大約三四年后,我就特別喜歡這個東西。當時也有機會去美術館看現代藝術了,特別是接觸到美國六十年代的繪畫、文藝復興早期的繪畫,慢慢就看了許多畫,建立起了一個比較系統的美術史的概念。
南都:這么說來,在你的學習里,其實很少有國學的東西。
張永和:我其實對國學缺乏了解,文言文也很差。我所謂的對繪畫體系的認識基本都是西方的。
我對中國古典的東西,建立在直觀的喜愛之情比較少。但前一兩年我在揚州看到一個古典園林,簡直是個意外的驚喜,特別喜歡。但這種情況很少。
南都:這次展覽中有你畫的峰火臺改造成客棧的草圖,很有武俠小說的意境,還以為你對中國古典式的東西有情結。
張永和:這個挺簡單的,我跟著老師學現代藝術,最重要的就是學杜尚。是他讓我認識到,藝術最有意思的是智慧,而不是美。剛剛說到“智”和“慧”的區別,如果“智”太多了,有時候有點太過于小聰明。至于在手法上到底是古典還是現代,對我來說并不重要。
長城的峰火臺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應該冒煙。以前是打仗的時候狼煙四起,是黑煙。而我覺得現在應該冒白煙,炊煙。何況我也不覺得古跡就應該是死的,而是應該繼續為人所用。這個改造應該跟古長城的峰火臺建筑還是統一的。
南都:你在80年代的草圖還有許多有意思的,比如把一部電影做成建筑是什么樣,還有畫自己的狀態、愛人的狀態,把男人畫成一個長著兩只腳的胃,女人畫成爐子。這非常有冥想的感覺。
張永和:(笑)其實現在大家最熟悉的一些人物比如扎哈·哈迪德(2004年普利茲克獎獲得者,著名建筑師)等人,在80年代初的時候都是這樣,他們當時還沒蓋起房子。他們就畫畫,畫建筑畫。
今天的學生看到的作為他們榜樣的建筑師都是在蓋房子,而我們那一代人看到的榜樣都在畫畫、寫書。像雷姆·庫哈斯(2000年普利茲克獎獲得者,CCTV新大樓設計者)當時是一個作家、思想家,所以我們也沒有必須要蓋房子的壓力。
至于我,是因為后來越畫圖就越想蓋房子,后來那個欲望非常強烈,就開始痛苦了。覺得自己畫下去也畫不出什么,畫也覺得開始重復了,覺得自己的思想沒推進。我當時覺得如果能畫得出新意,我的建筑能往前推動,就不妨接著畫。可當時開始迷失方向,不知道該往哪兒走。
所以你看看以前的東西,再看我今天的作品,就不會問為什么這個人想起來跨界。你說的這個草圖,它其實也是雕塑。你說是嘗試也行,其實我那會兒的狀態,跟現在的狀態相比沒有什么太大不同。
繼續閱讀:
下一篇:妹島和世擔任勞力士建筑導師
編輯:shx
推薦
花邊
排行
專題
平面設計
工業設計
CG插畫
UI交互
室內設計
建筑環境
中國設計之窗 © 版權所有 粵ICP備09030610號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news@333cn.com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news@333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