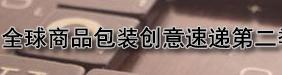雙訪張永和:警惕與診斷
作者:333cn.com 來源:333cn.com :
二分宅與鮮魚口
“前門鮮魚口的項目,我覺得做得不怎么樣,業主也覺得不怎么樣。將來這個房子蓋好了,裝的是新生活。連開發商都能夠想到,人到這兒來,其實是吃喝玩的,不是來看一個博物館。”
南都:你近年來的作品,比如說“長城腳下的公社”,你現在還喜歡嗎?
張永和:喜歡。對所謂院宅,我一直特別感興趣。其實興趣這詞也不太對,我小時候在院宅里生活了多年。其他的住宅類型,盡管我也住過,我從來也沒在一個房子里,再住過十三年。怎么對待院宅,院宅跟環境是什么關系,院宅的設計過程是怎么操作的,這些問題的回答都在二分宅(是“長城腳下的公社”的12座住宅之一)里。
南都:中國的院宅有什么跟現代住宅不一樣的地方嗎?
張永和:其實就是有兩點。一,全世界到處都有院子,院子并不是中國獨有的,中國的院子是一個沒頂的生活空間,也可以說是一個沒頂的起居室。可是在這個空間里能夠擺著桌子吃東西,小孩能夠玩兒,甚至可以修個自行車等等。這是一個能夠生活的室外空間。二,它跟自然有接觸,中國的四合院全都有樹。去歐洲的有些城市的院子,它是沒樹的。中國的不能沒樹,北京的所謂的四合院存在跟自然的關系。上面有片天,下面有塊地,中間有兩棵樹。當時我們家離王府井特別近,從王府井走到了自己家的院子,實際上是從城市、街道回到自然的一個過程。
根據這兩點,二分宅強調院子里頭有樹。盡管實際上,二分宅后來成了酒店,而沒有成為真正的住家,我設計時頭腦中的生活場景可能沒有真正發生,可是實際上,它是可以發生的。
南都:你說這個,讓我想起王澍說過,一些建筑師的作品,后來被改得亂七八糟。使用方根本不在乎建筑師本人的想法是什么。你遇到過這種情況嗎?
張永和:遇到過。實際上,這個問題根本不是針對建筑師的。一方面是整個的社會文化修養比較低,另一個與中國的文化意識有關,我們的文化中是新舊不分的。一個法國哲學家講中國的時間概念與歐洲不一樣,歐洲的時間是分段的,中國人的時間是連續的,沒有過去和將來,始終活在現在。我也不太懂,我覺得這說得挺有道理的。
日本也是這樣,人家新舊不分是怎么樣呢?就是把一個老的神社,隔二十年重建一遍。可是那個新的和老的一模一樣。
在咱們這兒,往往他說原來那個不夠好了,咱們現在造一個更好的,什么更好呢?比方說用料更高檔,裝修還要更講究等等。一改兩改就變樣了。過去與現在不分。所以像我父親的三河里“四部一會”(原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地質部、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聯合修建的辦公大樓)都給裝修了。那個樓是50年代蓋的,當時被人認為奢華,要反貪污反浪費,所以他挨批。后來又覺得不夠奢華,幾年前,整個給重修了。楊廷寶的和平賓館給毀成什么樣?
南都:這種濫改亂建的現象有什么辦法能改掉?
張永和:提高人的修養需要幾代人,根本來不及。實際上現在美國有很簡單的做法:任何房子,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房齡八十年以上就不能亂動了,既不能拆,又不能改。這是政府定的。意大利還短得多,比如說五十年以上,里頭可以動,外頭一點不許動。政府會派人拿著一張老照片,來跟你的房子對比,窗子、門、材料,表面全都不能動。我覺得,如果現在國家有這個意識,通過一些法規,是能夠去保護的。現在在中國還談不上。
南都:說中國的時間觀念里沒有過去、沒有將來,而只有現在,如果放在我們近二三十年的城市發展上看,這句話說得還是挺準確的。拆遷和不斷追新地建筑,不行再拆再改。所有老的都拆掉,都要最新潮的。
張永和:對,所以我有時候也懷疑自己是不是想法太西方化了。可是有時候總會免不了又覺得,文化這個概念是緊緊地跟歷史的。老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但怎么能理解到五十年、五百年?都得靠文物、建筑遺跡,各種實物。所以前些年王府井重新拆街,說這條街是七百年。我覺得真是荒謬,因為眼前的東西沒有一樣超過七年的。
南都:但是你自己也碰到這個問題了,你去做了北京前門鮮魚口的改造。
張永和:我們一開始就覺得很清楚,老建筑已經都沒了,那我們不能做假古董,因為做假古董就回到剛才說的那種局面了。
南都:對,所以你自己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怎么辦?
張永和:我面對這個問題,想到的就是恢復肌理,建筑外面當然要跟傳統與大的環境有一定關系,里面要做新院落。新院落必須做,它不是住宅了,而是商業區。但其實中間內部我們完全沒控制。
南都:這外界就不知道了。別人只會批評你。
張永和:其實有些人,真誠地認為做假古董是對的。但假古董最大的一個困境,就是它不能跟原來一模一樣,這就是大家不喜歡的它的原因,包括我自己。比方說原來一般的鋪面就是兩層,它有些特例有三層,可是現在大部分都是三層,那就不對了。
這個問題老發生。建筑師當然得有一個底線,到什么程度就不干了,因為建筑師只能做到這個,我沒有能力繞開業主直接就按我的想法干。
南都:沒法跟業主對著干。
張永和:這里面其實有一個非常艱苦的、長期的談判。我們把我們認為正確的想法拿出來。為什么說是正確的,并不是理想的?就是因為理想的可能還得往前走點。我們唯一的能夠耗點時間談判,這里面有時候也有一點點小退步。可是我覺得,做這件事從大局講是積極的。
前門鮮魚口的項目,我覺得做得不怎么樣,業主也覺得不怎么樣。在這里面———也是挺滑稽的事———反而是開發商比較能夠理解我們。你想,將來這個房子蓋好了,裝的是新生活。連開發商都能夠想到,人到這兒來,其實是吃喝玩的,不是來看一個博物館。而且前門的項目硬要算是個博物館的話,也是個很糟糕、很蹩腳的博物館。
這句話我覺得一定得說清楚,就是我覺得如果這些專家真的一板一眼地做傳統古建筑的恢復,就算缺乏一些合理性使用,也真沒得話說。要好好造一個博物館,也行。
南都:你還是把這事接下來,做了。
張永和:通過艱苦談判。可是有一點,不能放棄。現在做完了這些項目,后頭是不是還有北京老城的項目?所以現在希望是不是能夠好一點?因為建筑這個事,如果僅僅是為了表達一個立場,我就寫篇文章得了,這是于事無補的,變成了一個旁觀者。那還不如自己參與這個工作。就算蓋得只好了一丁點,我也覺得這更是一個建筑師參與社會的一個方式。
“前門鮮魚口的項目,我覺得做得不怎么樣,業主也覺得不怎么樣。將來這個房子蓋好了,裝的是新生活。連開發商都能夠想到,人到這兒來,其實是吃喝玩的,不是來看一個博物館。”
南都:你近年來的作品,比如說“長城腳下的公社”,你現在還喜歡嗎?
張永和:喜歡。對所謂院宅,我一直特別感興趣。其實興趣這詞也不太對,我小時候在院宅里生活了多年。其他的住宅類型,盡管我也住過,我從來也沒在一個房子里,再住過十三年。怎么對待院宅,院宅跟環境是什么關系,院宅的設計過程是怎么操作的,這些問題的回答都在二分宅(是“長城腳下的公社”的12座住宅之一)里。
南都:中國的院宅有什么跟現代住宅不一樣的地方嗎?
張永和:其實就是有兩點。一,全世界到處都有院子,院子并不是中國獨有的,中國的院子是一個沒頂的生活空間,也可以說是一個沒頂的起居室。可是在這個空間里能夠擺著桌子吃東西,小孩能夠玩兒,甚至可以修個自行車等等。這是一個能夠生活的室外空間。二,它跟自然有接觸,中國的四合院全都有樹。去歐洲的有些城市的院子,它是沒樹的。中國的不能沒樹,北京的所謂的四合院存在跟自然的關系。上面有片天,下面有塊地,中間有兩棵樹。當時我們家離王府井特別近,從王府井走到了自己家的院子,實際上是從城市、街道回到自然的一個過程。
根據這兩點,二分宅強調院子里頭有樹。盡管實際上,二分宅后來成了酒店,而沒有成為真正的住家,我設計時頭腦中的生活場景可能沒有真正發生,可是實際上,它是可以發生的。
南都:你說這個,讓我想起王澍說過,一些建筑師的作品,后來被改得亂七八糟。使用方根本不在乎建筑師本人的想法是什么。你遇到過這種情況嗎?
張永和:遇到過。實際上,這個問題根本不是針對建筑師的。一方面是整個的社會文化修養比較低,另一個與中國的文化意識有關,我們的文化中是新舊不分的。一個法國哲學家講中國的時間概念與歐洲不一樣,歐洲的時間是分段的,中國人的時間是連續的,沒有過去和將來,始終活在現在。我也不太懂,我覺得這說得挺有道理的。
日本也是這樣,人家新舊不分是怎么樣呢?就是把一個老的神社,隔二十年重建一遍。可是那個新的和老的一模一樣。
在咱們這兒,往往他說原來那個不夠好了,咱們現在造一個更好的,什么更好呢?比方說用料更高檔,裝修還要更講究等等。一改兩改就變樣了。過去與現在不分。所以像我父親的三河里“四部一會”(原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地質部、重工業部、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機械工業部聯合修建的辦公大樓)都給裝修了。那個樓是50年代蓋的,當時被人認為奢華,要反貪污反浪費,所以他挨批。后來又覺得不夠奢華,幾年前,整個給重修了。楊廷寶的和平賓館給毀成什么樣?
南都:這種濫改亂建的現象有什么辦法能改掉?
張永和:提高人的修養需要幾代人,根本來不及。實際上現在美國有很簡單的做法:任何房子,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房齡八十年以上就不能亂動了,既不能拆,又不能改。這是政府定的。意大利還短得多,比如說五十年以上,里頭可以動,外頭一點不許動。政府會派人拿著一張老照片,來跟你的房子對比,窗子、門、材料,表面全都不能動。我覺得,如果現在國家有這個意識,通過一些法規,是能夠去保護的。現在在中國還談不上。
南都:說中國的時間觀念里沒有過去、沒有將來,而只有現在,如果放在我們近二三十年的城市發展上看,這句話說得還是挺準確的。拆遷和不斷追新地建筑,不行再拆再改。所有老的都拆掉,都要最新潮的。
張永和:對,所以我有時候也懷疑自己是不是想法太西方化了。可是有時候總會免不了又覺得,文化這個概念是緊緊地跟歷史的。老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但怎么能理解到五十年、五百年?都得靠文物、建筑遺跡,各種實物。所以前些年王府井重新拆街,說這條街是七百年。我覺得真是荒謬,因為眼前的東西沒有一樣超過七年的。
南都:但是你自己也碰到這個問題了,你去做了北京前門鮮魚口的改造。
張永和:我們一開始就覺得很清楚,老建筑已經都沒了,那我們不能做假古董,因為做假古董就回到剛才說的那種局面了。
南都:對,所以你自己面臨這個問題的時候怎么辦?
張永和:我面對這個問題,想到的就是恢復肌理,建筑外面當然要跟傳統與大的環境有一定關系,里面要做新院落。新院落必須做,它不是住宅了,而是商業區。但其實中間內部我們完全沒控制。
南都:這外界就不知道了。別人只會批評你。
張永和:其實有些人,真誠地認為做假古董是對的。但假古董最大的一個困境,就是它不能跟原來一模一樣,這就是大家不喜歡的它的原因,包括我自己。比方說原來一般的鋪面就是兩層,它有些特例有三層,可是現在大部分都是三層,那就不對了。
這個問題老發生。建筑師當然得有一個底線,到什么程度就不干了,因為建筑師只能做到這個,我沒有能力繞開業主直接就按我的想法干。
南都:沒法跟業主對著干。
張永和:這里面其實有一個非常艱苦的、長期的談判。我們把我們認為正確的想法拿出來。為什么說是正確的,并不是理想的?就是因為理想的可能還得往前走點。我們唯一的能夠耗點時間談判,這里面有時候也有一點點小退步。可是我覺得,做這件事從大局講是積極的。
前門鮮魚口的項目,我覺得做得不怎么樣,業主也覺得不怎么樣。在這里面———也是挺滑稽的事———反而是開發商比較能夠理解我們。你想,將來這個房子蓋好了,裝的是新生活。連開發商都能夠想到,人到這兒來,其實是吃喝玩的,不是來看一個博物館。而且前門的項目硬要算是個博物館的話,也是個很糟糕、很蹩腳的博物館。
這句話我覺得一定得說清楚,就是我覺得如果這些專家真的一板一眼地做傳統古建筑的恢復,就算缺乏一些合理性使用,也真沒得話說。要好好造一個博物館,也行。
南都:你還是把這事接下來,做了。
張永和:通過艱苦談判。可是有一點,不能放棄。現在做完了這些項目,后頭是不是還有北京老城的項目?所以現在希望是不是能夠好一點?因為建筑這個事,如果僅僅是為了表達一個立場,我就寫篇文章得了,這是于事無補的,變成了一個旁觀者。那還不如自己參與這個工作。就算蓋得只好了一丁點,我也覺得這更是一個建筑師參與社會的一個方式。
繼續閱讀:
下一篇:妹島和世擔任勞力士建筑導師
編輯:shx
推薦
花邊
排行
專題
平面設計
工業設計
CG插畫
UI交互
室內設計
建筑環境
中國設計之窗 © 版權所有 粵ICP備09030610號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news@333cn.com
Tel:0755-21041837 客服:serve@333cn.com 資訊提交:news@333cn.com